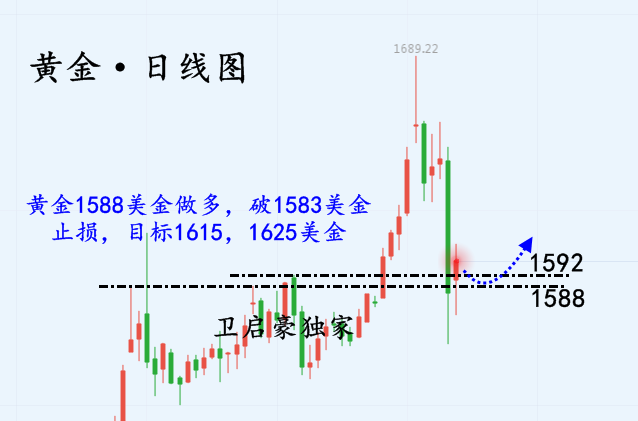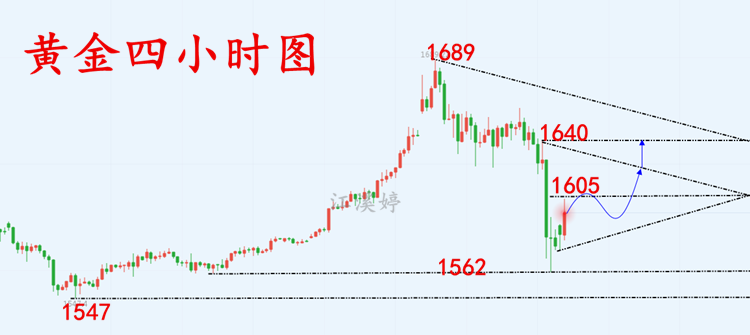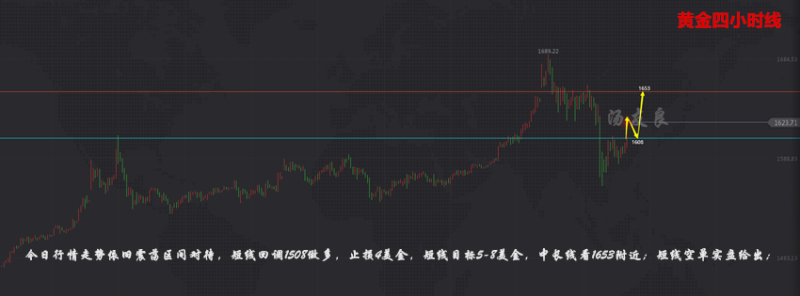哈罗德·詹姆斯
要理解' 欧元危机,显然需要懂点经济学。此外还需要懂点欧洲各国深层次的文化取向。
时值夏休季' target='_blank' >高峰,正好可以了解一下欧洲的闲暇文化。欧洲人玩和放松的热情,不亚于他们在金融和经济上打拼的劲头。问题不仅仅是他们做什么。他们怎么做,尤其是谁做的,有助于揭示欧洲难题的深层性质。
今年6月的欧洲杯似乎很乐意让自己被看成欧洲单一货币危局的影射。人们说被淘汰的队伍是“脱离' 欧元区”。希腊人则自豪地见证了他们的国家队挺过小组赛,杀进四分之一决赛。
意大利和德国之间的半决赛成了一个兆头,捅破了德国总理' target='_blank' >默克尔打算向意大利让步、支持后者国债市场这一层窗户纸。意大利总理' target='_blank' >马里奥·' target='_blank' >蒙蒂很快得名“超级玛丽”,更有媒体给他“移植”了一个莫西干头——在半决赛两度攻破德国人球门的意大利球星马里奥·巴洛特利的招牌发型。
欧元隐喻不仅出现在绿茵场上。巴伐利亚州歌剧院有个一年一度的歌剧节。在今年的歌剧节上,歌剧院新编了充满末日氛围的《众神的黄昏》——' target='_blank' >瓦格纳四联剧《尼伯龙根指环》的第四部。剧中,厄运缠身的角色骑着一匹摇木马,其形状是一个金灿灿的欧元符号。舞台布景也变成了现代玻璃幕墙,一会儿表现某家银行的总部(灯光打出“利润”的字样),一会儿表现时尚的购物圣殿。剧终的大灾难也成了一场金融危机,腐败的银行家被彻底消灭。
按照导演安德列亚斯·克里根斯堡的诠释,欧元就相当于瓦格纳笔下的指环,是权力的象征,这一嫁接反映了欧洲范围内广为流行的一种阴谋论——欧元,就像尼伯龙根的指环一样,是莱茵河地区的生意人借以主宰欧洲的工具。
这部歌剧其实是马丁·沃尔夫、乔治·' target='_blank' >索罗斯等人所鼓吹的一种欧元危机观的翻版:德国不遗余力地谋求出口盈余,导致了欧洲和全世界的厄运。按照当今德国批评者在金融媒体上的说法,那种权谋终究是脆弱的。在舞台上,一切以德国的方式结束——恐怖与毁灭。
这样来解释瓦格纳并不是破天荒头一次。甚至早在19世纪,社会主义作家和评论家萧伯纳就曾雄辩地解释说,瓦格纳的《指环》其实是资本主义崛起和衰落的一个寓言。瓦格纳曾致信巴伐利亚疯王路德维希,抨击金融的腐败(尽管当时银行家的收入远不及瓦格纳从国王那里获得的犒赏)。而他关于末日浩劫的想象,也许来自他在1848年革命时,同俄国无政府主义领袖巴枯宁在德累斯顿并肩作战时的体验。
导演的意图并非歌剧的全部。就像足球一样,歌剧的成败也取决于人员的配备和场上表现。评论家早就指出,在绿茵场上,欧洲各国的国家队高度依赖移民球员的贡献:北非之于法国,波兰、土耳其之于德国等。巴洛特利的父母是加纳人,而在半决赛为德国队攻入一球的梅苏特·厄齐尔则是土耳其移民的第三代。
无独有偶,歌剧也反映了欧洲面临的类似问题。当欧洲沉浸在音乐之夏的欢愉之际,你可以观察一下音乐家的出身,欧洲的越来越少。
慕尼黑版《指环》中的两位齐格弗里德——均为杰出的歌唱家——来自北美。歌唱成了全球化进程的另一个缩影,而欧洲人似乎在这个领域也在失去阵地。
一代人以前,为意大利' 世界杯开幕式献唱的是意大利超级男高音帕瓦罗蒂。另外两位同台演出者则是西班牙歌唱家卡雷拉斯和多明戈。“三大男高音”清楚地显示了,歌唱是旧大陆的强项。
而当今的世界三大男高音——比利亚松、库拉、弗洛雷斯都是拉美人。新一代歌唱家只是声乐全球化大潮的冰山之顶而已(慕尼黑版《指环》中最具魅力的演唱者是《齐格弗里德》中木鸟的扮演者,俄' target='_blank' >罗斯女歌唱家韦洛兰斯基)。
对这一现象的解释并不在于培养体制和登台演出的机会发生了什么转变。在这两方面,欧洲仍具优势。公共资金运营的小剧场是年轻歌者开始职业生涯的理想场所,而年轻的美洲和俄罗斯歌者纷纷到德国和意大利去一试身手。
实际上,这一现象的解释更宽泛也更具有警示意义。它是人才全球化和欧洲之外教育水平提升两种趋势相结合的产物。面对激烈的全球竞争,欧洲的年轻一代丧失了斗志,消磨了动力和雄心。
在西欧以外,歌唱新秀辈出,为了成功,他们愿意牺牲。欧洲的音乐后进则太安逸、太自满,不愿付出足够的辛苦,以发展自己的潜能。这一命运,也许既关系到欧洲歌剧的未来,也关系到欧元的未来。
[作者系普林斯顿大学历史与国际事务教授、欧洲大学研究院(佛罗伦萨)历史学教授。翻译:马俊。Copyright::Project Syndicate, 2012.]
 客服热线:
客服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