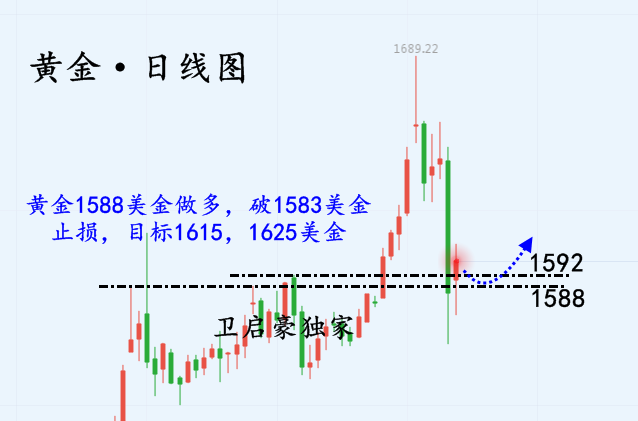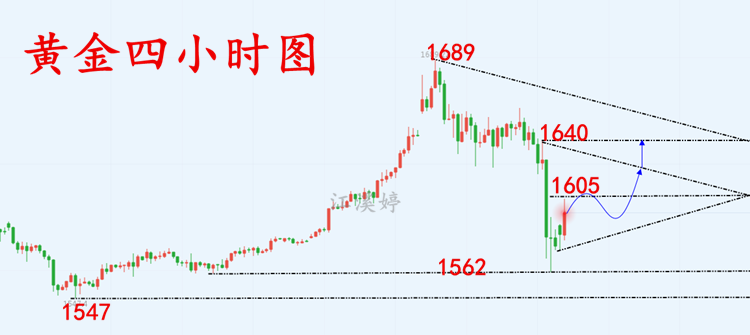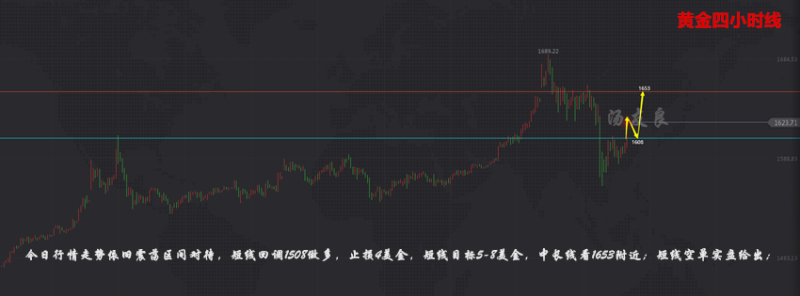改革开放30年,TCL集团也走过了27个年头。27年里,这个在广东成长起来的企业经历了品牌、战略、产权等一系列的改革,是许多中国企业从小到大,逐渐成长、发展和壮大过程的代表,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画卷中的一个缩影。
作为TCL的缔造者,李东生无疑是中国' 家电制造业的领军人物。作为国企改制的成功标本,我们从TCL集团惊心动魄的改制中能观察到什么,又能借鉴到什么?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专访了TCL集团总裁李东生。
第一个梦想:“车间主任”
记者:作为赶上中国改革开放年代的一代人,今天你的梦想实现了吗?
李东生:这个问题比较大。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考上大学,考上大学可以离开农场,可以到企业去工作,对我自己来说绝对是改变命运的一个机会,当时很高兴,很兴奋。
毕业时没有那么大的梦想,我的第一个梦想是做车间主任,然后当厂长。这个想法在当时也是比较朴实的,我先加入TCL的前身TTK(家庭电器有限公司)公司,才四十多个人,但是抓市场机会抓得比较准,效益不错。1982年左右盈利非常好,有了第一桶金,再慢慢有资本做投资,发展到电话机、录音机,再做电视机,一路扩展开来。
大学分配本来是分我到机关的,我不太想去。到TTK是我自己找的,当时没有几家电子企业,这家企业的老董事长说好,你过来,我就过来了。因为公司很小,当车间主任的梦想一年半之内就实现了。当总经理时我才28岁。
记者:如果把TCL置身于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背景下,TCL的发展和成长分成哪几个阶段?分别有什么特点?
李东生:我参与筹办第一家比较有规模、有竞争力的企业,是1986年底和香港的“' 金山”以及飞利浦三家合资的,这也是飞利浦在中国投资运作的第一家工厂。投产的时候飞利浦的总裁专门到惠州,当时坐企业自己的专机来,很轰动。不管是企业规模还是管理水平,当时都是无与伦比的。
步入上世纪90年代,TCL企业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TCL的名字在中国真正做起来。
记者:如果总结经验,你觉得最关键的是什么?
李东生:第一,品牌方面我们觉醒得比较早。我在广州第一次听到CI,听了之后觉得很有道理,就做了CI手册。记得当时一页纸是2万元,但是后来发现引进CI帮助很大。这是成功很重要的原因。
第二在产品上的工艺设计能力。生产大屏幕彩电,是找准的一个市场突破口。
第三是改制。1996年,我担任了TCL集团的总裁,政府领导支持,让我们做一个产业体制改革的方案。我们做调研,参考一些法律、规定、政府文件和早期改制企业的做法,提出以“授权经营,增量奖股”的方式来推进企业的改革。这个方案设计得很成功,有效营造了企业内部的一种激励和约束的机制。此后企业高速成长,竞争力也快速提高,规模和效益都翻了几番。
同学三人执掌三大彩电企业
记者:创维的黄宏生、康佳的陈伟荣和你是华南理工大学的同学。你们三个同时在一个时代掌控三个彩电企业,你认为这是巧合吗?
李东生:我觉得应该是时代的现象。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发展最快的是消费品;而消费品中,电子消费品是最重要的产业。我们大学毕业时都会给自己定个目标——过多少年要买一台彩电或者是冰箱。
所以这个市场的空间是最大的,而我的同学中学电子的多,黄宏生是我同届、同专业的同学。所以都聚集在这个产业里,很正常。2000年以后,' 互联网等产业发展速度更快,我们这个产业就没有那么风光了,也很正常。
记者:你领导的TCL是一家国企,黄宏生领导的创维是一家民企,在同一个产业,同一个市场中,你感觉你们各有什么优势和弱势?
李东生:TCL并不是传统的国有企业。1996年之前TCL股权是100%归地方政府持有。但是,它并不按照国家的体制运作,国家给你投资给你项目你层层报批,不是这样的。我们按照市场来办事。所以我们有国有的性质,但企业运作的模式更多像一种民企的机制运作,政府也基本上不参与、不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
在改制以后,更加是名副其实的控股公司了。现在国家还是最大的股东,占12.7%。这是我们跟创维最大的区别,创维一开始是民企,黄宏生个人以及他的家庭占的股份是非常高的。
记者:国企和民企的区别,可能很重要的一点是,国企刚开始会得到银行资金的大量支持,这是国企的优势。
李东生:对,这在上世纪80年代体现出来了。我们办电话机厂,钱都是借的,90万元的投资我们占了70%,当时是政府的官员带着我们到香港借。政府官员出面签字,等于说是变相担保了。所以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资金方面地方对我们帮助很大。没有这一点,我们早期的原始积累没有这么快。但是上世纪90年代后,国家的银行管理就很规范了,这个优势就不明显了。
2001年才把房契收回来
记者: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在你前后有很多的企业家都想做,但是很多都没有成功。你认为你成功是什么原因?你说过与当时当地政府的开明有关,是吗?
李东生:很多的因素结合起来才可以成功。首先政府认可这个事情,看到这样做对企业好。第二,你设计的方案要多赢,对各方面都要有好处。第三,你要合法、合理。当时我们和市里的领导汇报方案,有一个原则很清晰——方案的条款不违反法律和法规的。规定不让做的事情一定不能做,不能挑战;对于没有规定的,你要肯定是否对各方都有利的,是否公平。
在我们上市的过程中,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公司,都经过很严厉的法律审核,也经过了法律部门严格的审核。小问题还是有一些。但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另外,我们的改制让各方得到了很大的好处。比如国有资产快速增长,对当地经济快速提升,企业效益的改善,不单体现在所有股东的回报改善上,更重要是对当地经济贡献能力有提高。改制之前我们一年大概交税1亿多元,5年改制后交税10多亿元;同时规模和效益同步增长,给当地带来了就业机会。
所以有关方面才会把我们的体制改革作为一个改革的模式。很重要的是当地政府当时的高瞻远瞩,看到了改制对企业的好处。大家得到的东西都超过了原先发展的平均水平,超过了原先的期望值,这就没那么多争议。
记者:你当时有个人的压力吗?
李东生:压力挺大的,当时做TCL的改制方案需要交50万元的风险金,如果这个项目做砸了,这50万元就没有了。这笔钱是我个人出的。我把我自己的房子和我父亲的房子都押给政府,作为授权经营的风险抵押金,直到2001年才把房契收回来。
真正改制的过程中,不会动个人资产,新的资产增量时,按照一定的比例给你,然后交税,你再买成公司的股份。等于钱我没有收到口袋里,但还是赚了。在整个流程上,按照当时的法律法规都是比较严谨的。每年核算下来都由当地的审计局做考核,而且是累计考核,明年资产多了,相应的考核标准也就高一些。
记者:你一再强调合乎法规这一点,相信这是国企改革中很重要的环节。
李东生:体制改革的各种方案,我碰到过很多——但一定不能动存量资产,因为转成股份的过程你一定要合乎法规。
记者:你如何评价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成果?
李东生:我觉得我还没有资格评价。国有企业的改革,总体来讲推进还是比较稳定的。整个社会各界对国有企业改革的认识程度差异很大。所以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一定要估计到社会接受的程度。企业改革能够带来变化和改革方案的设置有很大的关系。
当然,如果改革能够走得更快一点,可能会更好。但是国家大,认同差异也比较大。每次改革大家都可以看到社会的争议特别大,所以推进太快不见得是好事。在改革初期,我们根本就没有对外宣布政府内部的讨论协调方案,也是为了避免争议。改革有成果之后,才有限度地披露。
 客服热线:
客服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