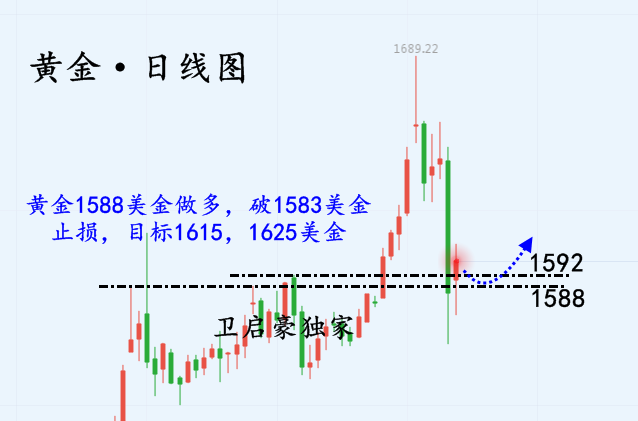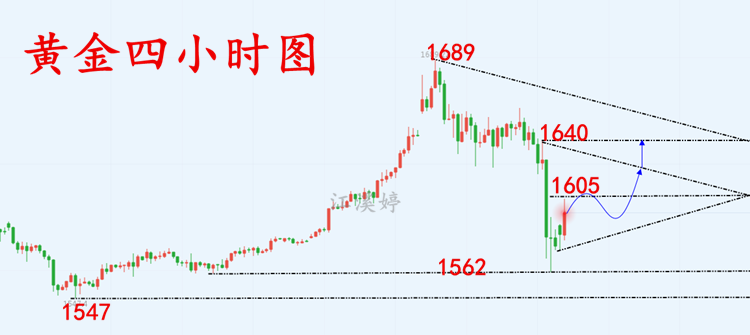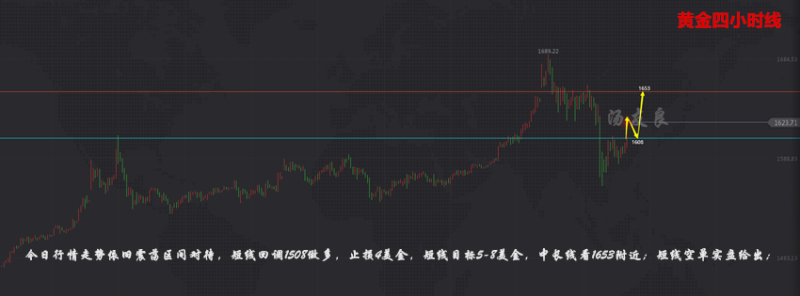好运Money+2012年第1期封面封面
【标题】你的职业梦想实现了吗?
几乎每个人都在念书时遭遇过这么一篇作文题目—《我的理想》,有的人只是随便对付过去,有的人却会认真地憧憬起来。那些认真写作文的小朋友在长大之后,往往又会遇到一群人对他们说:理想?忘了它吧!放低眼光,实际一点,工作就是挣一口饭吃。还有一种更高级的劝告:别把兴趣变成职业,你会更痛苦,更失望。
在任何一代人的父母辈看来,孩子们总是过于浪漫和不切实际的,在他们找到最终栖身的职业之前,一切尝试都可以叫做弯路。梦想最经常出现在那些弯路里。从结果的概率上看,老人们没有说谎,可当你还年轻,你舍得放弃你的职业梦想吗?
关于80后一代,有一句著名的误读,“他们更在意自我实现”,那其实是所有人的共性,只不过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因为父母积累了些许财富,自己肩上的责任较小,有更多选择的自由;他们中的大部分还是要面对现实的一轮轮挑战,高房价,职业竞争,日益狭小的城市生存空间。
我们邀请了四位不同职业的80后分享他们有关职业梦想和职业选择的故事,他们中间有人实现了梦想,有人中途放弃。从他们身上,你会发现,梦想成真不意味着完美,放弃也并不一定代表失败,梦想和现实的距离,是所有人都逃不开、要面对的。
郭兴(化名) 29岁
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
现在我是中央电视台的一名节目编导。
郭兴说:“我想我挺有代表性的吧,我的心路历程,可能好多人都有。”大学时代专业成绩优秀,一直把自己归为有理想、有冲劲的那一类,后来偶然进了电视台,做了一个自己并不喜欢的栏目,但每天听着父母把“稳定工作”四个字挂在嘴边,慢慢地就妥协了。工作7年至今,没有过任何变化。
温水煮青蛙,说的就是郭兴的故事。
郭兴就读的大学是一所艺术类院校,理想主义者的高发区。影视学院里每届都有一两个“青年伯格曼”和“小津安二郎接班人”;动画学院里的半数人都崇拜过手冢治虫;郭兴所在的录音学院,比较盛行的是组乐队,或者早早在外面的录音棚里打工。郭兴也组过爵士乐队,他的乐队还获过一些乐队竞赛的奖。
2005年,郭兴刚刚进入中央电视台的时候,他依然觉得自己将来是能干大事的。不过,暂时有那么一份工作也不错。
那工作,劳动强度不大,节目的一大半素材是从国外购买的,简单编辑一下就能用;国内拍摄的部分不贡献太多收视率,不好看也没人在乎;带着挂了CCTV台标的摄像机和话筒到了地方上,所有人都把他们当回事;一毕业就能拿到每月五六千元钱,比大部分本科生强;最重要的是,有正式聘用合同。做电视的人都知道,2008年以前,在央视,一纸聘书非常难求,老栏目的人员名额早就满了,晚来的编导只能做着“黑工”等待新名额出现的机会,常常一等三五年。郭兴恰好赶上了天上掉馅饼,他所在的是个新栏目,名额充裕。
唯一的问题就是他真的不喜欢这个节目,对整个频道的内容都毫无兴趣。栏目里闲散的氛围也让他有危机感,担心自己从此就废掉了。偶尔看到特别勤奋的编导,把行业分析得头头是道,心里还有点惭愧。他只能一直想着反正自己总有一天是要走的,想归想,却始终没动身。
“因为有这么一个小小的光环,一直不舍得离开,慢慢地就老了,我就29了。”
一段意外插曲险些让他真的摆脱这份工作。2011年初的时候, 栏目换了新领导,大概是由于新官上任三把火,领导对节目进行了一些激进的调整,郭兴跟领导对着干了几次,两人闹僵了。到6月的时候,他干脆不再去台里上班,连续在家里闷了几个月,10月,他的父母和岳父母出面干涉,终止了他的反抗。
工作出状况的时候,他正筹备着结婚。他和太太在2011年的11月11日领证,比原计划的时间晚了一些,原因就是他的工作动荡。不去上班,意味着没有片子做,没有绩效工资,中央电视台的基本工资每个月只有2000元,郭兴的经济状况窘迫了起来。
岳母在家里急得夜里睡不着觉,担心女婿失业,女儿跟着受影响;岳父是公务员,觉得职业稳定比什么都重要。郭兴说,大概很大程度上,对方父母也是看到自己是中央电视台的,比较靠谱, 比较体面,女儿嫁过来靠得住吧。虽然当时他的女朋友一直没有说什么,但这反而让郭兴既感激,又很有压力。他最终回到了栏目, 恢复正常上班。
赋闲时,他的父亲来找他恳谈了一次,问他,你觉得我们这一辈子干的是自己感兴趣的事吗?你觉得现在这个社会上有多少人干的是自己感兴趣的事,多少人不是?有一份稳定工作,别人看着还不错就行了—这话他太熟悉,熟悉到有时候他怀疑那就是他自己说出来的一样。
可能从他进入中央电视台工作的那天起,他就已经在认同着这种“稳定”的价值观了。郭兴几乎从未想过自己做音乐,那条道路太窄,走起来太艰苦。他的同学里坚持到现在的,只有一个人现在还算做出点儿成绩。当年班里的另一个出名才子,如今在给人做手机铃声,大部分人,不是转行了,就是还在“枪手”的道路上。郭兴说,音乐只能是个副业,在上面期待太多,很容易摔得很惨,“说到底我还是太看重保障了,这就是社会现实,如果生活在美国,我才不会在乎。”
就像两个鱼缸里的鱼,都觉得对方的水更甜、水草更丰满,郭兴会遇到许多羡慕他的人。周一开会,周二去露个面,周三编一天的片子,可能熬个夜,一周的工作就结束了,多自由,每个月还有差不多一万元钱的纯收入。可他说,我想朝九晚五,我想穿个西装在那里上班,有我自己的写字台,电视台里我只有一个柜子, 更别提个人电脑了。
可当他真的动手想找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时,却发现并不容易,他在家的几个月里,没有碰到一个动心的offer。有个奇怪的现象是,大学一毕业就进入央视工作并且获得聘用资格的人,很难从那里再离开。一方面本人会难以割舍那来之不易的聘书和央视的头衔, 另一方面外人也会认为,央视员工职业稳定、待遇好, 怎么舍得走?把你挖出来干嘛?郭兴所在的频道里有个挺出名的人,据说人面很广,三教九流都认识,一盒名片刚印完,不到两周就发光了。可好几年过去,他还在同一个栏目、同一个职位一动不动。郭兴的社交面并不宽,他的境况形同困兽。
郭兴喜欢经济、热衷理财,他曾经想过换个经济类的媒体,或者干脆去企业,从零开始。可他觉得想转到经济那行上,怎么也要去读个研究生,没准还得出国深造,否则就只能做站在银行门口对人说“先生我给您推荐个理财产品吧”这种事。这样的机会成本, 让他难以承受。
不是没有同事从央视离开,去了' 互联网公司做' 视频,虽然辛苦点,但收入更高。现在网络传播速度比电视快,郭兴他们去采访, 人家都更愿意跟网络媒体聊,说得推心置腹的。可他还是觉得那不是主流媒体,虽然外面的人都说如今互联网才是主流媒体了,他就是不承认。
“可能骨子里我还是个传统的人吧。”他说。
表面上看上去,郭兴并不是那么循规蹈矩的样子。他是那种挺潮的男孩,开很漂亮的汽车,懂钱包和服装的搭配。他和太太都是懂得享受生活的人,平时下了班两人总一起在西单闲逛,购物, 晚餐,每个月在外面约会吃大餐占掉他们生活支出的一大半。
郭兴的太太在一家事业单位工作,毕业求职的时候,她也曾经渴望去外企,还获得了不错的offer 。郭兴和她的父母一起苦口婆心地劝住了她。现在,两人结婚了,她也不再向往外面的世界,专心敦促郭兴努力前进。
郭兴也觉得自己应该还能再拼搏一下,抛开钱不管,关键是得学点什么,所有人都说年轻的时候别太在乎钱了。道理都懂,态度也很端正,但学什么、拼什么呢?表面上看来,郭兴暂时回到了职业正轨上,但他自己说,现在的他真的迷失了。
刘若琳 27岁
我从小就想当医生。
我现在是北京医院的康复科医生。
那种实现了职业梦想的生活又会怎样呢?刘若琳的生活就是这样。
1个月前,随着康复科一位病号的去世,刘若琳也结束了跟家属4个月的持久战,在传说中,大家都称这种情况为“医患紧张”。老大爷80多岁了,之前收治在呼吸科,由于年世已高,积极的治疗方案已经没有太多效果,家人托了关系送到康复科——理由是希望给老人更好的治疗环境,可是所有的医生护士们都心知肚明,在家护理将会为这个家庭带来多大的负担,不止是简单的金钱和时间的问题,并非所有的家属都能有足够坚强的心理面对长期卧床的亲人。
那些因为心脑血管疾病、中风而无法生活自理的病人不断被送过来,床位很紧张。医生劝病人的家属,将老大爷接回家。大爷的儿子,自称是研究医患纠纷的律师,不依不饶,把医生当做企图谋杀父亲的敌人一样对待,每过两三天就拉上老婆孩子在病房外的公共过道里大闹,上演一出医院见死不救的戏码。
刘若琳最怕每天早上的例行查房。那个病房里住着三位病人, 老大爷床位在中间,每次查完第一个病人,刘若琳的头就已经埋到白大褂里了,心里憋着火,恨不得自己能隐形,老大爷的儿子施施然坐在床边,一边削苹果,头也不抬地招招手,“小刘你过来,给我爸量个血压。”
在医院,每个新进医护人员的第一课,往往不是专业知识,而是医患矛盾。刘若琳说,几乎所有年头久一点的男医生,都有与病人打架的经验。在这拔剑弩张的紧张关系背后,有冷漠社会累积的不信任感,也是由于过度集中的医疗资源——刘若琳每周有7个半天的门诊,每次看30个号,这已经是最轻松的了,她在内科的同学, 每个上午看50个号,如果是外科,同样的时间,则要看100个号— 穿上白大褂之前无比庄严的誓词在来势汹汹的疲惫面前瞬时软弱无力,“我知道患者的每个问题都应该好好回答,但有的时候,你能理解吗?有一种再也不想说一句话的虚脱感。”
刘若琳1984年出生,北京人,北京大学医学部8年硕博连读毕业。她从小就想当医生,懵懵懂懂地向往白袍听诊器背后的权威感,医学院8年读下来,她身边不少同学都逃离了,她没撤,不是因为有多爱,纯粹是反射弧太长。在实习之后,她对医生这个职业还完全没有概念。
第一次实习是在大四,北医三院,晚上和住院医师值夜班。她被分配到呼吸科和血液科,都是夜班的重灾区,呼吸科的病人晚上容易呼吸不畅;血液病患者由于用药的关系,晚上容易出现发烧等应激反应。楼上楼下50多间病房,值班室里的呼叫灯响个不停。对每个值夜班的医生来说,回荡在楼道里的呼叫声,都像一组定时炸弹,你不知道它们什么时候会响起,爆炸在浅层的睡眠和脆弱的神经里。
状况处理得差不多了,刘若琳睡意全无,坐在值班室的床上, 心里反反复复只有一个念头,为什么那么辛苦。
研究生实习时,刘若琳碰上了自己第一个去世的病人。还是在呼吸科,病人是肺病晚期,晚上值班,家属呼叫说病人呼吸困难, 需要测心电图和血压。刘若琳赶到病房时,病人的脸已经憋成了酱红色,她和护士刚测量完就发现情况不对,就那么一秒的时间,病人的身体突然变软了,当时她慌了,开始实施抢救,但病人还是很快就不行了。
“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一个原本活生生的人,他的生命在一瞬间就被抽掉了。”每个医生心里都有那么一道坎,那种无能为力的感觉,刘若琳觉得自己至今都没有真正释怀。
刘若琳有一个女同学,是当年班里教授最得意的门生,毕业后分到了北医三院内科的风湿防疫科,每天从全国各地前来求医问药的,都是那些焦虑风湿病、红斑狼疮的患者和家属。对于这些慢性病,并没有特效药,医生能开的处方药也极少,想救却不能救的无力感,纠缠和消磨着新医生的理想。
还有与多年寒窗付出极其不成正比的收入水平。北京医院的待遇算是北京三甲医院里不错的,刘若琳这种级别的医生,在内科每个月到手的钱不过3000多元,外科更惨,一个月2000多元钱。这是怎样的收入概念?医院食堂里随便一小碟土豆烧牛肉都要卖到8 元钱。
刘若琳的这个女同学,家里环境不好,母亲常年生病。平时俩人吃饭,都是刘若琳请客,在纠结了几个月之后,她毅然决定辞职, 应聘去了一家比利时医药企业在北京的代表处,月收入过万。
他们班一起读到博士毕业的同学,现在已经流失了三成,他们很多出国,做研究,或者像这位女生一样,在国内找了起薪很高的医药行业的工作。
经过现实的一轮筛选之后,剩下的,要么是真正热爱,要么是对医生未来的回报期望值很高的年轻人,比方说外科诊室里最常出现的那些。每位成功的外科医生都必须具备一定的狼性,下了班谁也不会走,扎堆等着急诊的手术机会,哪怕只是观摩,或者有幸在边上帮主刀医生抬病人大腿。
刘若琳属于第三类—北京本地人,没有经济上的压力,她喜欢这个职业,可是没有办法忍受外科初级医生的那种煎熬。于是, 康复科的主任在毕业生中一忽悠,她就选择留在了这个听起来还很新鲜的科室。有别于传统科室,这里设置了很多像健身房一样的器材,工作环境相对简单,大多时间能按时上下班。
她也遇到过单纯为了稳定的生活而在医院里煎熬着的医生。每次护士和他汇报病人的状况时,他能推就推,“再看看”、“再等等”,一位资历老的医生都看不下去了,劝他说,你就不能去病房看看病人吗?
刘若琳不能理解。几个月前,他们科室收治了一位因为脑血栓而有行走障碍的老人,一个月后出院时,老人已经能正常行走了。每次病人和家属对她说,“小刘医生,我们都听你的”,她会有一种心里落满阳光的感觉。
虽然她一直说,“好像实现了理想也不过如此”,但她也觉得,这就是生活吧。
胡玥 24岁
我曾经想做了不起的文字工作者。
现在我是个律师。
前两天,胡玥和朋友在北京木马剧场看话剧。台上的中年男主人公面目纠结,情绪激动,他的台词是:20岁的时候,觉得自己真牛,全世界就他最牛,但现在,才发现当年自己那是傻。胡玥不以为然,“哥们儿,你现在才认清这个事实吗?那我比你要早清醒太多了。”
胡玥现在在北京某律师事务所工作,新晋律师,主要做IPO业务。最近还多了一项工作,她和几个新员工一起“承包”了公司的年会,从采购、节目安排到流程都建立了专门的Excel表格,标明进度,很有律师的职业风格。
胡玥披着一头软软的长头发,一直长到腰际,外表看上去是一副文艺女青年的样子。和现在的同事一起去看小型的摇滚演唱会时,同事不停地看手表,抱怨为什么表演不能按时开始,音响声音太大了,耳朵都震得流耳油了,以及这种表演为什么不能按时地结束。换做以前,她会认为这个人好俗,没法交流,可现在她会说, 是啊,有道理。
她自己都不相信她能从事这么一份正常且靠谱的工作,她很得意客户对她的评价,胡律师开会的时候,也是人模狗样的。
胡玥有个网名,叫浅灰色橡皮,13岁起在天涯上写小说和散文,因为文笔出众,引起许多资深网友的追捧,在文艺圈里,早早就有了一些小名气。高中的她颇为心高气傲,成绩也好—父母和老师都说,你天生就是为了中文系而生的啊!
因为高考失利,她没有进入自己心目中最“阳春白雪”的第一志愿复旦中文系,而是考取了中国政法大学,来到北京。她给自己贴了个标签,学' 法律的人里文章写得最好的,写文章的人里最懂法律的。
毕业时,凭着圈子里的人脉和口碑,她轻而易举地进入了一家
著名报纸工作。
她做的第一篇稿子是奥运会特刊的人物报道,采访三里屯一家酒吧的老板。老板是个神人,大侃1980年代跳霹雳舞、1990年代办摇滚演唱会的精彩过往,胡玥觉得聊得很有料,文章肯定会很棒,但最后稿子出来时,她却慌了。她说:“采访对象那么有趣,我却写出一篇非常平庸的稿子,我对自己失望极了。”那篇稿子像一把利刃,刺破了自以为是下面包裹的某种现实—她有一定的天赋,但这点能量不足以让她在传媒这个行业里一鸣惊人。
她几乎是落荒而逃的,直至现在,也无法直面当时的心境和曾经的同事。自信又一帆风顺的她,从小被灌输的观点是,忠于理想。她的父亲是医生,在爷爷的逼迫下考了江西中医学院,当了一辈子的医生,却从来没有喜欢过这个职业。他告诉胡玥,做自己喜欢的事。
她喜欢写字,但她希望写出100分,一个70分的平庸者不是她想要的。
她开始考虑,要不要现实一点,回头当律师呢?
她去了某律师事务所面试。一轮笔试过后,只剩她一个本科生,四个合伙人坐庄面试她,一个看起来态度暧昧不明的中年男人在看完她的简历之后,只说了一句话,我觉得你更适合当记者。那份简历是她托一个记者帮忙写的,有超过五分之一的篇幅都在描述她文学上的天赋,以及发表过的形形色色的文章。
她还是不肯回到报社,于是意气用事,决定回头报考本专业的研究生。
两年后,2010年,她再度回到那家事务所面试,这一次,不再是退一步的选择,她做了精心准备。她把简历交给负责金融和法律的猎头朋友修改,再找了一个咨询公司的人帮忙看过,突出她英文与法律专业的能力,以及她研究生阶段的相关实习经历。
面试的时候,还是同样的那个态度不明的合伙人,“你花了两年时间从一个点努力走到另一个点,我们觉得应该给你个机会。”
这个合伙人,后来成为她最崇敬的一位律师。事实上,她是进入律所之后才得以近距离感知律师的真实状态,“他们都有着非常聪明的头脑,聪明到让人感动。”胡玥发现,在这群聪明且异常勤奋的人当中,她轻而易举地被洗脑了。她有时晚上8点打电话到别的律所,如果没有人接,她就下意识地觉得这个律所层次不行,而如果哪天按时下班了,她居然会生出莫名的羞耻心和焦灼感。
更重要的是,目前看来,她认为律师们对于自己的工作有一种普遍性的尊重。这正是她过去一直渴望却不曾获得的。
她在进入报社前,曾经和一位正在筹备新刊的主编喝咖啡, 那位主编很诚恳地劝她,“传媒这行,只适合特别想得开的人。”他告诉胡玥,中年之后,你和同一个起点的人会因为职业而产生差距和失落感;你身边的人在谈论的事情,你可能有一半都插不上话; 十年之后,你的同学开车来参加同学会,只有你是打车来。
不失望是不可能的,让胡玥恐慌的不是十年之后没有车开的生活,而是我们本该是伟大的战友啊!他怎么能以这种老油条的过来人语气来谈论我的梦想?她不止一次地假设过,如果当年,她碰到的是一个疯狂热爱新闻事业的记者,那结果是不是会不同?
未竟的理想偶尔会跳出来扰乱一下胡玥的模范职业状态。比方说,她得拼命抑制自己看到合同时就想顺句子、改修辞的生理冲动,学着用平淡且准确的语气,写出招股说明书。严格说来,律师属于服务行业,对于一个个性张扬的人,要收起所有的角翼装成无害的、面目模糊的中介人员,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一次她大咧咧将内部会议结论透露给客户,遭到领导苛责,带她的律师语重心长, 在一个高度紧张的行业,如果有人愿意花时间骂你,那就是在夸你,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另一种期待。
面对现在的工作,胡玥要承认自己并无天赋,也没有足够的准备,要努力放大一点点微小的进步来制造成就感,但在这种鼓励下,她愿意一试。
她希望尽快找到更强大、充分的理由支持自己前进。她开始悄悄研究自己身边的群体,他们为什么热爱律师这个职业?除了金钱之外?其实律师和会计师都是资本市场产业链里地位比较低的人, 但她确实认识从名校毕业进入投行,在投行实现了经济自由之后, 又转行做律师的人。这一年来,她还在寻找着这个问题的答案。
胡玥所在的事务所每年都会去政法大学宣讲,她跟着去了两年。据说,在之前,每年都有人问这样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要当律师?而从今年开始,学生们踊跃的提问变成了,你们的笔试都考什么?你们的起薪是多少?至少,她在做着一份让人羡慕的工作吧。
最近,下了班之后的胡玥还有一项额外工作,陪客户打三国杀。拥有自己的生活,对于职场“白骨精”来说,是否是重要的事? 对于这个横在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命题,被推上了轨道的胡玥并没有比别人想得更透彻。
王瑞睿(化名) 25岁
我想做个建筑师。
现在我就是。
晚上8点,北京某建筑事务所的门口还是停满了车,楼里透出的每个灯光下面,是一个依然在画图纸的建筑师。王瑞睿是其中之一。
王瑞睿,1986年出生,建筑学系毕业,工作三年。当建筑师,首先要满足一个先决条件,是否有过人的精力。这种' target='_blank' >高强度的工作从大学期间就开始,王瑞睿的毕业设计作品是北京南三环工业区旧厂房的改造,两个星期,每天早上5点睡,8点起床继续画。
至少从目前看,王瑞睿的人生还没有过什么大意外。父母是普通工人,从小在北京的胡同长大,家里往上倒数三辈,没有从事建筑相关行业的。他小时候喜欢看漫画,也喜欢写写画画的,家里一个姐姐随口说了一句,你报建筑系吧。
接下来发生的桥段,似乎应该是上大学之后的巨大失望— 由于在报考之前缺乏最基本的认知,这种状况在中国大学生的身上非常常见。可他是个异数,还有点励志。在上大学之前,如果可以选择,王瑞睿从来不看带字的书,但是进入建筑系之后,他每个月花1000多元钱买书不说,直至现在,无论下了班有多晚,都要看书到两三点才能睡觉。
到底是喜欢还是莫名其妙地相见恨晚,王瑞睿自己都说不清源动力在哪儿。可能是他对未来根本没有预设,宽容度就高很多, 如果当时他上的是计算机系,他觉得现在自己也将毫无悬念地成为一名爱岗敬业的工程师。
“我不敢说未来如何,但是建筑这件事,我做了8年,目前为止还没有厌倦。”他说学建筑最大的好处就是让他知道怎么玩能更好玩,比如说,他以前爱串胡同,到了哪都不闲着,现在知道了怎么去看出门道;有出国的机会,他看到一幢房子,会知道它是什么风格,大致什么年代建起来的。“别人都不知道,我就觉得很有优越感。”
王瑞睿长得很是高大帅气,也懂得在衣着上经营自己,经常画图的手指修长漂亮,总之,在这个建筑师被明星化的时代,你有理由相信,他有成为一名成功建筑师的本钱。
但他觉得“成功”这个目标太肤浅了,在中国,建筑师的圈子很小,如果你想成名的心够强烈,那去做些别人没做过的事哗众取宠,获得名气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而纯从物质角度来说,即使不做建筑师,他也有信心让家庭摆脱最基本的物质困扰—他和发小从小就喜欢研究古玩,上大学的时候,他俩倒卖了一块玉,挣的一笔钱抵得上他现在两年的工资。
有时候他和国外的建筑师朋友聊天,说起中国此起彼伏的高楼和遍地树立的钢筋脚手架,他们很羡慕王瑞睿,在这么年轻和资浅的时候,就有机会做一些大的项目—这些项目,在他们的家乡,建筑师可能一辈子就只有可能碰上两三个。可王瑞睿知道,中国的建筑体系是生产性的,即有规划有项目之后,再找建筑师来做,实际上建筑师可发挥的空间非常小,还要刨除业主和施工方因素的负面影响。不像在国外,会通过相对透明的过程和法规,削减掉很多不必要的人为因素。
他工作后接的第一个项目,是某二线城市的一个博物馆,当地的领导向他们提出来,希望设计一座复原汉朝风格的建筑。
如果建成,那将是审美水平一再挑战公众智商的另一座建筑物。王瑞睿说,这样的要求提出来,肯定有建筑师愿意屈从于不菲的设计费,完全遵照甲方的原有设想;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说,中国还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现代建筑的革命,你没有理由要求非专业背景的人拥有足够的鉴别能力。
王瑞睿并不是不想挑战固有的思维制式,但他的状态明显太超前了。他有一个朋友想建一座寺庙,找到他帮忙画设计图,他设计了一座现代建筑,“为什么寺庙一定要长成飞檐彩栋的样子?” 朋友反问他,如果寺庙变得很有设计感,还会有人进来烧香吗?
至于那个复原成汉朝的博物馆项目,在他老板的斡旋下,当地官员终于放弃了原来的想法。这种胜利,在建筑师与甲方的众多隐形较量中,非常难得。
他们大学的同班同学,只有两三个改了行,其他人都选择了与建筑相关的工作,建筑事务所、官方设计院、或者房地产开发公司设计部。这在所有的毕业生里,几乎算原有专业流失率最低的了, 这不能排除优厚待遇的天然吸引力。设计院几乎都解决户口,外地来的同学会为了北京户口“卖身”,至于北京当地的毕业生,王瑞睿和高中同学聚会,毕业三年,同班同学混得好的,也不过年薪10 万左右,而他们建筑师,能达到他们2至3倍的收入水平。
但王瑞睿拒绝从这个庸俗的角度阐述自己,他在认真实现自己的理想,建筑师这个职业维系着他现在的努力与对未来的所有期待。
王瑞睿想自己开一个小一点的事务所,就像日本很多建筑师一样,有自己独立的工作空间,过着三天打渔两天晒网的生活。不是懒散,也是出于现实的考虑,独立出来的建筑师很可能接不到活,只能从家具设计做起。
他当然也希望成为现状的突破者,哪怕最后成功是他人的,自己只能成为这条路上的铺路基石。这种心理准备,他也有。
他的工作,既有暴露在外的光鲜,也有背后的艰辛。他圣诞节去英国度假,但在此之前,得连续几个月颠三倒四地炼狱加班完成手头的项目。在最辛苦的时候,他还是会每个月去一两趟“鬼市”,那是北京报国寺附近的一个' 收藏品地下交易场所。他可能早上五点多钟就起来,去看一两个小时,再去上班。他什么也不会买,好像只是为了寻找一个工作之外的出口。
他有一个表哥,很年轻,27岁,从小就立志在公务员系统里闯出一片天地,他结婚特别早,好像是23 岁,当时王瑞睿不解,干嘛这么早把自己困住,表哥说如果是单身青年,在他们系统里很难得到提拔。结婚之后很快就生了小孩,现在孩子2岁,家庭稳定,他也顺利地升到副处级。这无疑是一个太过现实的典型, 但是每次家庭聚会,王瑞睿看他抱着小孩,也是一副很知足的样子。通过他,王瑞睿相信,能目的明确地一条路走到黑,应该也是一种幸福。
 客服热线:
客服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