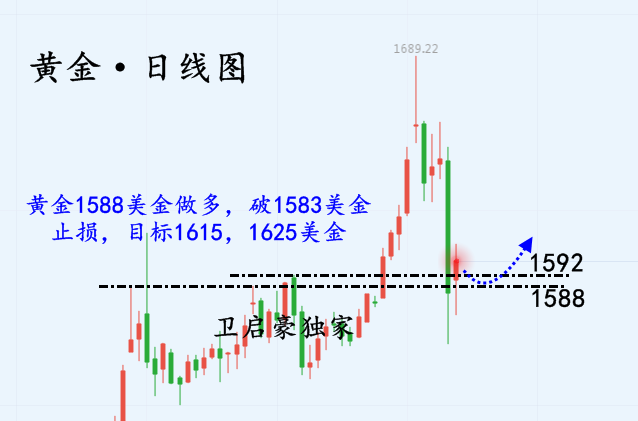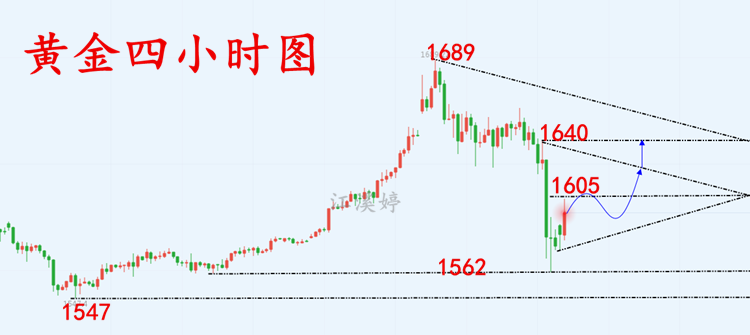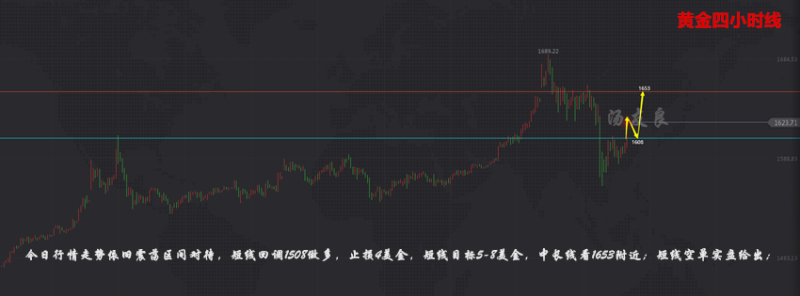【口述实录】
13年前,我在最好动的年龄躺倒,得了白血病。我被推进病房,闻着刺鼻的酒精味,看到一个又一个光头小伙伴……对未知的恐惧远比痛苦的治疗过程骇人。这时有个医生对我说:“我看好的像你这样的孩子很多,现在有的出国读书,有的当了医生……你对自己要有信心,也要对我有信心。”
这位医生,是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血液肿瘤科副主任薛惠良,我至今忘不了他坚定的眼神。他没有骗我,4年后,我出院,回到校园;7年后,我工作了;如今,我正准备出国留学,也当一名医生,是我此生最大的梦想。
病来如山倒
很突然。发病两周前,我参加了一个同学的追悼会,他得白血病去世。两周后,我开始发烧,高烧不退,吃退烧药也没用。
那是1999年夏天,我14岁,念初中二年级。
当父母意识到这不是普通的发烧时,我已几乎昏迷。送院急诊,血常规显示:白细胞4.5万(正常范围是4000-1万)。迷迷糊糊中,我听到有个医生说:“这孩子"白粉"好高啊!”后来我知道了,“白粉”是白细胞的俗称,而“白粉很高”的意思是“高度怀疑白血病”。当时我在家里附近的一家二级医院,急诊医生叮嘱:“赶快去三级医院进一步确认!”
找到也在家里附近的一家三甲医院,住院一周,骨髓穿刺结果却是“各项指标正常”,无法确认为白血病;可我的白细胞指标还在飙升,达到了9.6万……
无法确诊,治疗就无从谈起。躺在病床上的我情况每况愈下,一身身汗把厚厚的床垫一层层浸湿;不几天,我都坐不起来了。
“去儿童医学中心看看吧!”医生建议。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上一年才成立,引进了一批进口检查设备。一周后我转诊到那儿,被血液肿瘤科副主任薛惠良和他的团队收治。跟别的许多表情严肃的医生不同,他永远笑嘻嘻,小孩都不怕他,叫他“薛伯伯”。后来我才体会到,他是真心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那时,好多次他出门诊,却总赶在8点门诊开始前跑来病房给我们一一做当天的骨髓穿刺,因为孩子都说他做骨穿不痛。
我就在那群孩子里。在儿中心做完第一次骨髓穿刺检查,我正式住院。根据那次骨穿报告,我被基本确诊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还因为我已超过10岁,而且白细胞指标超过10万,属于“高危患儿”。但父母对我只字不提病情。当时我的床头卡上写着“慢粒待排”(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有待排除,这也是一种凶险的白血病),妈妈却笑着说:“你看,这是肺结核的意思,很容易治的!”但我心里清楚,很恐惧。其实我一住进病房,看到这里80%的孩子是光头,再想起去世的那个同学,已经基本有了答案。
百米冲刺跑
化疗开始,我出现了大面积溃疡,从嘴巴到食道,只能“打点滴”送营养;溃疡逐渐消退后,改成插鼻饲管,营养液从鼻腔送入食道……这样过了两周,我挠挠头,抓下一把头发。我求护士姐姐给我理发,也剃成了光头。
我是病房里最大的孩子,因为“懂事”,除了忍受化疗带来的肉体痛苦,更要强忍心理折磨。我曾经跟着爸妈看过《血疑》,主人公最后死了,因此觉得这个病“没救”。我开始排斥治疗。
化疗第一个疗程结束后,我被推入胸片室,确认溃疡引发的肺部感染情况。当医生让我抱住拍片仪时,我突然失去知觉,休克倒地卧床1个月后突然站起,导致了低血压。妈妈见状当场瘫在医院走廊里,大喊大叫。此时,一位正在门诊的医生冲出诊室……多年后,妈妈每次忆起这个场景,都很激动,“是薛医生!他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到了你身边!”她总对我说,永远不能忘了薛医生,他是救命恩人。
薛医生个头不高,走路常常托着腰,病友们都知道他有腰疾。我想,那一次的百米冲刺跑,或许真是医生的救人“本能”。
那天深夜,我苏醒后第一个看到的就是薛医生。他明白我的心事,微笑着说:“我看好的像你这样的孩子很多……你要对自己有信心,也要对我有信心。”
我的情况真的好转了,白细胞回落,病情缓解。我开始接受小化疗,不用长期住院了。薛医生给了我他家里的电话,那时手机还没普及,他以这种方式守护着我们这群孩子。
2003年做最后一个疗程时,我嘴馋吃了甘蔗,当夜发烧、休克。一通深夜的求救电话,一个不眠夜,我第二次在抢救室苏醒,第一眼见到的又是薛医生。
第二次人生
我是一个幸运儿。得病4年后,停止了化疗,进入5年随访期。收拾东西准备出院时,薛医生严肃地对我说:你一定要回学校读书;有空常回医院看看,给其他小患儿打打气!
我原先是个不爱上学的孩子,得病前是老师头疼的“皮大王”,打架滋事、“无恶不作”……工读学校的车子曾经停到了我家门口。但薛医生的话,我要听。休学多年后,我戴着鸭舌帽回了校园。那年,我的物理笔记被贴到板报上表扬,教导主任说:“阿俊,你真的变了!”
我考上了中专,又读夜大拿到了大专文凭,目前就职于一家国际航空公司。
我曾迫切地想考医科,在医院里待了这么多年,我无比怀念那个充满酒精味的地方;我得到过那么多医生的救助,我想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现在,我以另一种方式回了医院,如薛医生希望的那样,我成了白血病病房的志愿者,用亲身经历鼓励弟弟妹妹们。
第一次当志愿者,我发现薛医生当年真的没骗我我遇到了比我年纪还大的志愿者,也是当年的白血病患儿。薛医生真的看好了好多孩子,也因为这样,他的病人越来越多我们大了,早已超过了儿科医院的就诊年龄(18岁),但因为得过特殊的病,更因为信任他,我们的“号”会一直挂在他这里;得了病,总由他初步判断病情,提出一个供参考的治疗方案,我们再去成人医院寻求治疗。这实属他的份外事,但他从不推辞。
他就是这样一个儿科病房里的“好好先生”。要说这么多年有什么改变,唯一的就是他白头发多了。我们全家最大的心愿,是如果有一天我结婚,一定要请薛伯伯当证婚人他给了我第二次人生!
 客服热线:
客服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