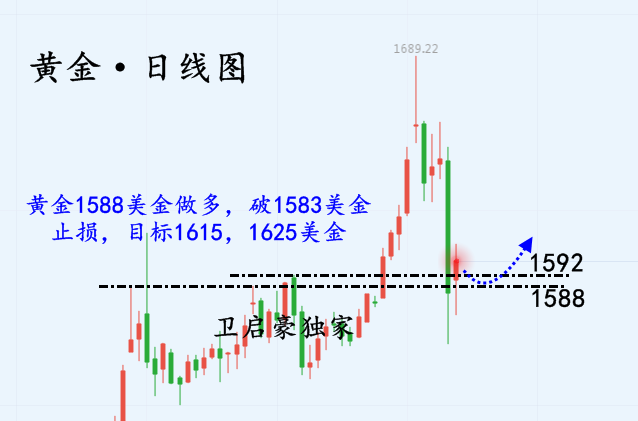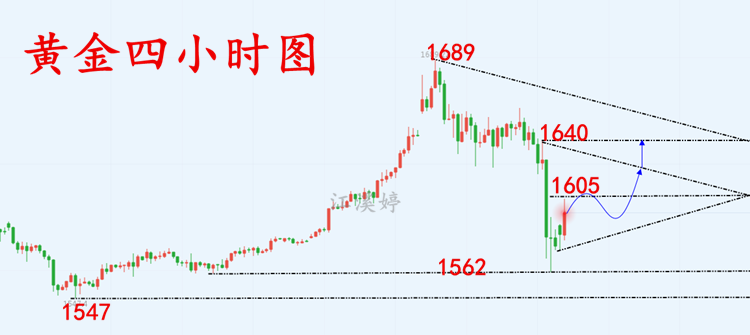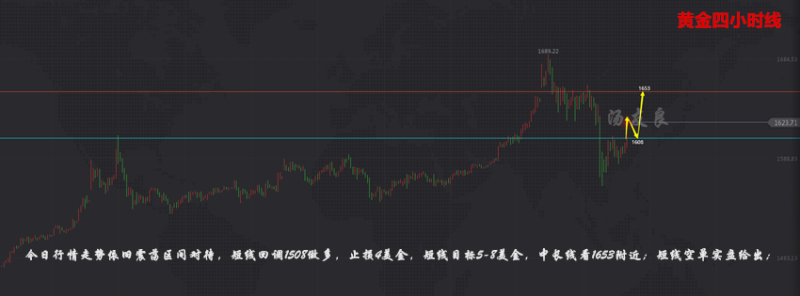艺术与财富 郭成
2014年4月28日,“废墟——李纲水墨方式的再解组”展览在广州国际单位艺术中心举办。同期举办的研讨会上,批评家、策展人和美术馆等多个领域的专家围绕本次展览以及李纲作品,进行了精彩的座谈。研讨会从作品、艺术家、策展方式、展览形式等各个角度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以下是部分批评家研讨会发言内容:
贾方舟
这个展览和我最近想的问题完全一样,特别突出的是展览方式和过去的经验不一样。过去策展人具有明确的身份,他是要在艺术家现成作品的基础上策划展览,而这个展览中,策展人杭春晓参与了整个创作过程,与艺术家进行了一次合谋。
我觉得不一样的地方:如果区别这两种身份的差异,看成是知识生产,那么艺术家更接近原生产,策展人更接近生产组合。
我整体看李纲作品的时候,当然是去捡拾某一块砖头。这个砖头拓印的过程,杭春晓没有亲自做,但是实际上参与了意见。我判断策展人的好坏,列了四个标准,但是现在看起来这个标准破掉了,所以我对这个问题有兴趣。这四个标准是:第一,对当代问题的发现,能够把握住当代问题,这个你做到了。第二,找出一个非常明确的主题。第三,选择非常适当的艺术家。第四,展览的布局,让你能实现这个主题。作品呈现的结果是策展人参与的意见比较多。这个展览应该是这样的案例:从总体来说,就是一个策展人和艺术家共同创造的作品。综合呈现特别重要,如果只是呈现拓片,那倒没有什么意义。同时展示其过程,包括拓完了以后,砖的样貌,这个非常有意思。
皮道坚
在我所接触到的“废墟”题材的当代艺术作品中,这是一种很新的呈现。首先,它跟以前关于“废墟”的呈现不一样,带来很多东西,这是我的第一个感受。第二,我一直强调水墨应该是开放的水墨,这些年水墨向各种当代艺术样式植入,但这次行为装置这样大型的综合性植入,我是第一次见到,觉得非常震撼。他和以前的不同在于,他通过四个环节提取转换,从不同的角度,把我们日常世俗化的形象,从无意识的状态变成一种反思。“废墟”有象征性。为什么巫鸿他们对“废墟”感兴趣?因为当代艺术非常象征化,很多人说中国是一脚踏着过去,一脚踩向未来,过去和未来并存。他选择了“废墟”,这是非常形象的反思。
殷双喜
李纲的作品运用了“拓印”这个概念,是给传统注入新意。过去,我们的前人拓印碑帖,那是把历史通过拓印流传到今天,是一种对过去的追忆和怀念。
改革开放以后,当代艺术家有拓印长城的,也是向历史致敬。李纲的拓印关注的是废墟,是城市的碎片。他通过拓印,把这个现实送进博物馆,他有没有传到将来的愿望,现在不好说。但是,艺术家做的工作就是点石成金的工作。所以艺术家说这个是金子,就是金子;但是你要相信,你不要去搞化学检验,这是信仰领域里的事情。再一点,李纲采用的方法是一种博物馆的方法,就是像威尼斯双年展的概念,建立起一个虚拟档案,把这个现实进行编号,呈现出一种档案的形态。
王璜生
今天我第一次这么完整地看完李纲的这组作品。我觉得他是很有勇气和智慧地进行着转型,从原来的那种“水墨方格”平面走向了一个多元综合,包括影像、立体、行为等,这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探索之路。他通过对水墨废墟、文化废墟的隐喻,借助于砖头的符号,以搜集、提取、编号、拓印、再造、转换等过程与方式,综合行为、平面、影像、光效等,构成一种很强的“气场”、很强的一种力量,从而形成了一个可以更多地进行文化阐释的空间。
王林
关于李纲的作品,我想做两个比较。
一个是八十年代东北艺术家王长白等人做过的实物拓印。李纲的拓印用砖头,尽管也是实物,但仍然把拓印返回到水墨形式的表现力之中,这和他长期从事抽象水墨创作有关。这里有一个层面可以研究,就是从实物拓印到抽象水墨的变化,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另一个比较,是在今年威尼斯展览中,艾未未的一个作品也叫《废墟》。他采集在汶川地震灾区建筑的钢筋,拉直,堆积,做了一个非常有体量感的装置作品。很干净、很有力量,有几何抽象这种属性,但背后又有强烈的社会针对性。把这个作品和李纲作品做个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一种趋势,就是社会的针对性在艺术中是怎么转化成为现场感受、怎么形成艺术氛围的。这是让参观者重新在场,而不仅仅是废墟本身在场。
所以说,李纲的作品是一个祭奠,是对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上最大废墟之地的祭奠。
杨维民
细细地看李纲现在的作品,实际上他是拿那种废墟的砖,不是在做拓模,他是把废墟的砖挥洒如笔,已不单单是在拓印。那些宣纸画深深的墨痕、遒劲迸溅的墨汁,是他触摸残砖碎墙而升腾的内心激愤,他的悲情坚毅地表现出来,这是一个精神自虐之物化置换。我认为李纲不是一种拓印,因为他不是在直接复制和简单再现。我们以前的拓印是把经典的东西,比方说古代碑文、印玺铭文拓印成文本,是一种原封不动的复制,是一种直接的清晰再现,从而再次传世阅读。李纲是把人们不可能认为是文献的东西,创造为一种新文本,把他放进了美术馆,也就是把现实的废弃,用水墨文化造就了一种仪式,幻化为文本文献,也就把废墟之残砖堂而皇之物化为历史文献。
' target='_blank' >王春辰
今天的艺术家常在创作中使用多种媒介,比较盛行跨界。跨界在今天为什么成为一种需要?实际上,这意味着艺术家思考艺术和生活的拓展和深化。原来的“墨痕”展是一个客观中立的态度,只是看到抽象形式的问题。今天李纲把拓印的方式发展到观念的层面,发展到对社会现实中,记录着中国社会变化的场景,这些都是媒介的扩展。各种媒介的互为使用,对艺术家的挑战程度更高,远远超出单一媒介的艺术家的能力。我们本身在美术馆工作,经常看到各种媒介同时使用,很多情况下给艺术家带来了启发和想象。这个废墟具有双重的意义,一个是现实的废墟,一个是在载体背后的历史的废墟,如此构成他想以水墨的方式来表现废墟的意义。在今天,艺术家如何把跨界做得更深入,这是另外一个挑战,这恐怕不是一次展览能完成的。我们在这里对李纲老师表达期待。
吴鸿
我们今天所身处的这个时代中,特定的社会景观、人心的欲望和人类文明史中一以贯之的乌托邦理想,构成了李纲展览的社会性背景。从策展人的角度看,这个展览因为策展人的介入,从而使展览的形态和方式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个好的策展人不是在艺术家的作品基础上进行再解释,或者充当艺术家的老师,而应该把展览视为自己的作品,通过运用空间,在展示艺术品的过程中,用策展人的语言对艺术家及其作品进行重新阐述。当代艺术的话语系统有自己的游戏逻辑,以艺术家为中心所建立起来的个人和乌托邦的想象,今天的展示形式似乎给他们带来很多不利的条件——每个展厅分散,互相之间不贯通。然而,今天每个展厅的分割对于策展人的解组而言恰到好处,因而在策展人的学术逻辑系统里,这个展览并不是孤立的个案。
杨卫
我认为单是社会学的转换还不够,因为毕竟还是艺术,我们要从艺术形式与艺术语言上去理解,而不是只谈它的社会性与现实性。刚刚看了这个展览的几个板块,我发现这些作品的形式感也很强。当然,这种形式感是区别于传统水墨方式的。首先是打破了传统的单一模式,李纲在展览中穿插了多种语言,比如影像、装置、照片以及拓印方式,等等。从语言的角度看,正是多种方式的介入,重新激活了水墨画,而将水墨方式运用到当代语境中,也是对当代艺术媒介的一种丰富。这两者是互补关系,一方面将水墨方式用到当代语境中,重新发挥;另一方面是运用当代的各种视觉元素,来重新激活水墨画。最后呈现的结果非常丰富,形式感很强,也很艺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水墨画还是有很宽很长的路可以走。
唐克扬
中国还处在一个没有完全被西方的现代艺术所侵蚀的状况之中,但现在这个趋势必不可免,因为每个人创作时,首先想到的因素不是意趣,不是概念,而是一个具象的东西,如材料、空间等。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方面,我们创作的物质和以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古代的中国没有废墟的概念,不是因为过去没有废墟,而是因为过去怀古。今天大家对世界轮回不是很在意,楼房建好之后,又费劲地拆掉,产生了大量的废墟。当李老师用水墨的材质,制作一种带有城市、建筑含义的作品时,实际上是他本人对生活环境、人生经历的一种回顾。这个废墟是双重的,更多的是在他的生活经历之中,对某种变化的追忆,还有对于水墨这种材料的坚持。这可能是讨论废墟的一个重要的出发点。
吴洪亮
中国现在是一个盛产拆与废墟的时代,这个展览空间是一个先解后组的空间。作为一个美术馆人,我对展览本身、对如何利用展览空间资源,来表述艺术家以及策展人的态度很感兴趣。这个展览是在进行了周密的阴谋后的艺术家和策展人的共谋,所以这个展览很有趣。我觉得李纲老师跟春晓,好像已经把我们现在能想到的关于当代艺术的游戏,在这个展览里穷尽而且延续了,甚至可能还会在一年以后或者更长时间,给我们呈现一些再想象。
刘礼宾
针对这个展览谈四个点。
第一个,李纲类似做了一个功课——用一个展场激活了一个词。“提”、“取”、“转”、“换”,我们用一个展场去看这样一个词的时候,特别有助于对这些词的理解,每个词负载的文化含义可能被激活。第二个,我看重三个元素的统一:动作、动作所提示的物质以及他们的身体,三者构成怎样的关联?在李纲的平面作品中,我能看到这三者。今天的展场,我看到的是“动作”和“物质”这两个关键词,我期待下一步,有没有可能有身体的介入?第三个是“废墟”问题。擅长某一艺术形式的艺术家都在进行“介入社会”的努力,我更看重的是从艺术本体出来,从其特征延伸出的社会介入性,水墨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李纲在这方面做出了自己的努力。第四个,我比较喜欢第四个展场,这个展场展现出了特殊的品质。我觉得经过九十年代的“实验水墨”和“新文人画”,“水墨”最紧要的问题不再是表现纠结于中西的视觉游戏,或者展现才情,而是你让观众看到作品品质的时候,让人理解到中国人特殊的主体建构的时候。
鲁明军
策展人杭春晓提出的"提取转化"给人的一个初步感觉是,他把现在最流行的,或者说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以来的当代艺术手法,基本上操练了一遍,里面有形式、有观念、有关系美学、有社会介入,还有点人类学的色彩,等等。实际上,这都是今天在整个国际艺术界,我们非常熟悉的艺术语言。在这个意义上,他实际上以李老师为一个对象,在做一个测试,看看水墨还有没有其他可能性,毕竟在水墨界这种尝试还是不多。关键是,我看到的一种精确度。对每一个东西,他还是力所能及达到一种精确度。但是,我的质疑也恰恰在这里,好像还是试图把李老师放到今天流行的当代艺术框架里面。其实,我们所期待的恰恰是李老师的这种实验,有没有突破这种既有体系的可能,准确地说,有没有太多意外感。这也是我们下一步的期待。
盛葳
李纲先生有非整体性、单元化和元素化的东西,这可能能够对应策展人关于解组的含义。但是我想,其实它也有一种可能,这些砖头的元素可以组成新的建筑,但是没这样做。建构一种新的、平行的、民主的秩序,一种非差异化的多项意义再生产,这个非常重要。最后一点,这种定制的方式,无论是砖头,还是水墨单幅的作品,实际上跟圆圈的规律化、定制化,秩序上是一致的,在这一点可以建立艺术家在差异化之外的一种连续性的脉络。
段君
这次展览“废墟”不是衡量展览价值的最大因素,衡量这次展览价值最大的因素还是工作的方法,就是李纲强调的转换,这个层面比较重要。这就是为什么刚才问你们之间有没有相互不能妥协的地方。这次展览看起来是沟通比较顺畅的结果,如果展览当中有一些沟通不畅的领域在这个展览当中呈现,也会很有意思。另外,在展览里面,我们更多的是看到了方法转换,而且刚才几位专业的批评家也看到了李纲对水墨本身的控制,这种能力是他作为职业艺术家的能力,也很细微。
 客服热线:
客服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