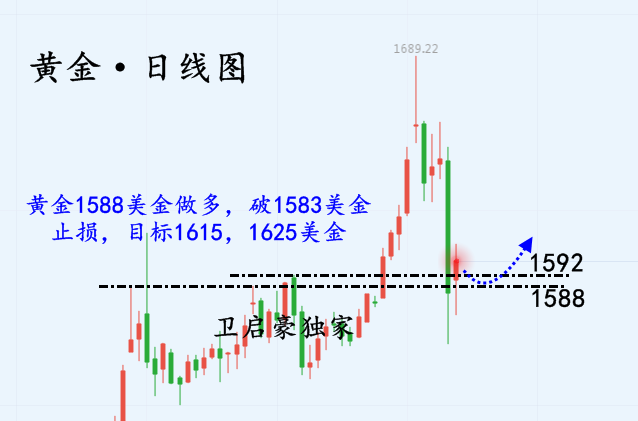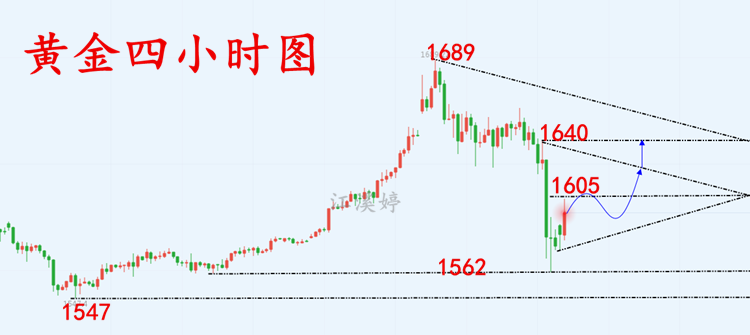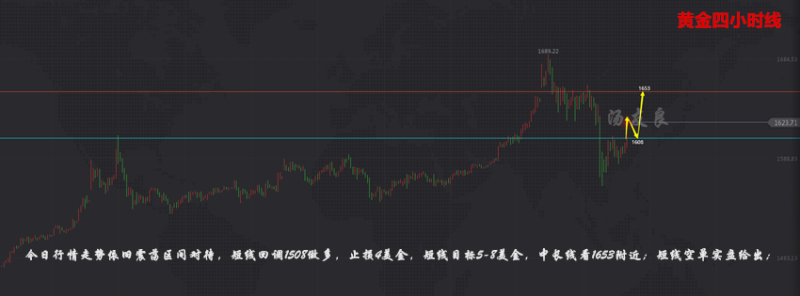“你不要说你是新华社记者' target='_blank' >吴晓波,只要告诉你是吴晓波就行了。”
当面前的企业家对他说出这句话时,第一次,青年吴晓波的心里响起一声惊雷:个体价值崛起的时代开始了。这位企业家喜欢吴晓波的文字,在报章上追吴的专栏,对他而言,他看重的是“吴晓波”这个名字及背后的人,而非其他。在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名字前面带着一个前缀:“单位”,他们的荣辱得丧与其密不可分。单位是一把放心的保护伞,但一不小心也会变成一个坚实的牢笼。
从那时候起,吴晓波开始每年写一本书,买一套房,以惊人的自律和勤奋在“建立自我”的大道上一路狂奔。他将写字视为自己的本分,迄今,二十多年的坚持,和同龄人相比,他成了这条路上寂寞的独行者,也成为享有盛名的记录者,所到之处,谁人不识君。但不止于此,他不屑做一个传统型的拙于谋生的文人,买房、做出版、玩自媒体、卖酒、搞投资,这些紧跟时代脉动的商业探索行动,让他可以穿Giorgio Armani西装,坐头等舱,住四季酒店,在“党国要人”' target='_blank' >张静江当年住过的西湖别墅里办公;让他成为“一个亿也很难收买”的独立观察者,成为一个具有争议也具有极大丰富性和可能性的“文人”。
和企业家打交道几十年,他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私下来往并不密切,但他绝不排斥自己成为这个群体的一份子。“像我这样蛮少的,很多知识分子面对金钱保持一种清高的姿态,形成一种反商业的态度。我热爱金钱。”吴晓波点燃一支烟,言辞坦荡。
在“自由知识分子”时期,他和权力也曾经隔着一条河的距离。如今,他和地方政府一起做基金,在总理座谈会上建言献策,在吴晓波频道年终秀上坚定看多中国。他很明确,这是一个李敖所谓的“政治挂帅,经济挂帅,知识分子不帅”的时代。
只是偶尔,在烟雾缭绕中,他也会想起若干年前的自己。那时候,他烟抽得不凶,当众演讲还有点羞怯,为' target='_blank' >李普曼与沈从文的文本沉醉,批判不合理的现实图景“纵笔所至不检束”,看着窗外的京杭大运河遥想这座城池在宋朝时的水村山郭、杏花烟雨……。这时候,这个被很多人喜欢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已到知天命之年的男人往往有些疑惑:自己到底喜不喜欢现在的自己?
企业家要不要做“公知”?
问:《激荡十年,水大鱼大》这本新书提到一个观点,企业家与公共意见领袖之间的界限在模糊,' target='_blank' >任志强等一批企业家都有公共表达的属性,但这一拨人现在都已经隐退,没有继续发挥这样的作用。
吴晓波:我十几年前写过一本书叫《被夸大的使命》,当时的观点是企业家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界限是清晰的。企业家是商业利益的生产者,知识分子是思想的生产者,这两种身份很难兼容。
这几年,全球范围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在技术领域。基础设施破坏以后,实际上造成整个商业秩序、社会秩序和文明秩序发生极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其实都不是经典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在第一时间感知到的,反而是提供这些变化的企业家、商业观察家,最早预知的。
198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在公共意见表达方面,基本上没有大的影响力。商业投资人、硅谷的一批人,还有一些科学家,是他们提出了人类未来的变化。中国其实也蛮明显的,像' target='_blank' >马云、' target='_blank' >马化腾这些人冲在变化的第一线。这就模糊了知识分子的身份,他们本来是愿意在公共市场中表达自己专业思想的人,讲究逻辑,现在变成企业家在这一方面能力很强。
像任志强有两面性,他一面性是地产商,但大家并不只把他看成一个卖房子的人,而把他看成是' 房地产的观察者或研究者,这其实就溢出了他作为一个企业家的身份。他又超出了房地产领域,做了很多关于中国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评论。
四十年来,企业家阶层的整体出现,是中国社会发生的最重大的事情。它比所建的任何高楼大厦都重要得多,造就了千万人级的有产阶级。这部分人在财富积累的同时,一定会表达公共意见。
到今天为止,这部分属性具有特别大的争议性。
2015年,' target='_blank' >柳传志在正和岛提出在商言商,是一个拐点事件。
问:很多企业家比较强调本分、自保,你觉得企业家有没有可能成为建设新环境的主导性力量?
吴晓波:像柳总这样的人是代表性力量。一个社会的公共思想市场,如果是由企业家来主导,或者其突破需要企业家来完成,这是一个过高的期望,也完全不可能实现。一个大学教授和一个企业家,如果同时受到惩罚,它的后果的最大区别是——教授失去教职,但企业家可能会造成1万户家庭的失业。
德鲁克在《企业的性质》里写,企业家要做几件事情:
第一,提供合格的产品;
第二,合法纳税;
第三,善待员工;
第四,与周边的社区环境形成良好的关系;
第五是慈善。
做好企业是企业家的本质工作,企业家本身的角色不承担推动公共秩序进步的责任。
问:有些企业家得到官方的很多荣誉,但还是觉得国家给予这个阶层的认可远远不够。你怎么看?
吴晓波:我觉得没必要,企业家就要做好本分。如果一个企业家需要国家认定他是一个功勋人物,这是很扯淡的一件事。
很多企业家参政议政、做' 两会代表是自我意愿,尽了一个公民的责任,但不能因为没有这个机会,就觉得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和嘉许,这是错误的;也不能因为当了人大代表,就觉得被外部认同,自己是一个好企业。
企业家若真觉得要表达一些意见,可以捐款给一些基金会,请人做课题,在专业领域表达意见。
在国外,对一个优秀的企业家来说,参政和做慈善是同一件事情,无非是在不同领域做表达。找专门的人成立慈善基金会做慈善,像' target='_blank' >巴菲特把钱给了比尔·' target='_blank' >盖茨基金会,比尔·盖茨现在成了社会企业家,这其中也会体现企业家精神。国内的,像' target='_blank' >马蔚华从' 招商银行(' 600036,' 股吧)退休后,花了很多精力做慈善型、公益型事业。他们这都属于非常职业的表达。
问:您长期关注新中产,这个新的群体在政治、文化方面,有什么新的特点与诉求?
吴晓波:中国的主力工业人口是80后、90后,而80后绝大部分受过四年制的本科教育,还有相当一部分接受过西方教育,他们对现代社会和公民社会的民主、自由、法制是有基本认知的,属于准中产阶级,这是我们对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盘认知。
但是,用列宁的话来讲,中产阶级是最脆弱的,因为他们的生存压力很大,一旦失去工作,就有可能离开这个城市,不知道去哪儿。或者在无产阶级革命家看来,他们又是最庸俗的,天天想着房价、柴米油盐、小孩读幼儿园这类事情。
中产阶级不断扩大以后,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走到马路上呼吁中国的民主制度建设,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中国的知识分子长期以来对财富和企业家阶层有一种巨大的敌视态度和对峙状态。
像我这样蛮少的,我自己热爱金钱,又做财经研究。大部分人面对金钱保持一种清高的姿态,形成一种反商业的态度,这最容易获得同情。当这变成一种公共姿态以后,企业家和知识分子之间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裂痕。
随着技术的变革,思想供给开始从纯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蔓延到商业阶层,而商业领域的人从自己的专业出发,愿意做公共表达,这些人反倒成为思想上的供给者。当这些变革开始发生以后,这两个群体的角色已经开始模糊。
 统一的新闻市场,已经丧失掉了
统一的新闻市场,已经丧失掉了
问:现在您做商业,有意约束自己的公共表达了吗?就写作题材而言,之前写了很多公共话题,后来是不是会偏商业议题?
吴晓波:会的。当任何一个东西变成商业机器的时候,这个主导者一定会有很多的畏惧,我其实也一样。
问:' target='_blank' >科斯说“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是缺乏思想市场”。现在自媒体的整体勃兴,对这个问题有突破吗?
吴晓波:还不到。我有一次与今日头条的人讨论这个事。他们说作家对思想解放与信息解放有很大的意义。我们长期的思想供给是有秩序的,原来所看到的信息是报纸、杂志。自媒体打破了这种秩序,造成两个景象:
一个景象是信息失控,人的选择时间增多。现在信息被分解,有些人可能天天关注快手、抖音、趣头条,有些人则选择一些严肃的东西,人的认知就迅速地差异化,实现分化。自媒体就诞生在这样的环境中,无非是选择为哪一群人提供一个片断的知识而已。今天中国统一的新闻市场,已经丧失掉了。比如之前大流感,我们都不知道今天的大流感和2003年的SARS之间有多大的关系,严重程度怎么样。从新闻报道来看,基本上是100:0的关系,当年铺天盖地都是SARS的事情,今天几乎是零。不应该是这样的,哪怕是100:20,100:17,100:75都有可能,今天就是100:0,新闻供给肯定出问题了。两年之前我写《那个最后的看门狗走了》,就像你看到的今天,最终受损伤的一定是公众,当媒体势力没有了以后,公众肯定受大损失。
另一个景象是关于一些重大问题的公众讨论已经不存在,或者说政策讨论的空间在丧失。中国现在有很多研究宏观经济学的人,论证中国崛起的重要性或者反动性,而很少研究像国有企业改革这样的具体问题、公共问题或政策。公共讨论的空间越来越空洞化,它是缺位的。
问:您之前写过一篇文章《敢死队犹在,特种兵已死》。现在好像已经没有多少调查记者,认真写稿子的人也渐少。但这个话题好像没引起足够的重视,很多人看不到这个危害。
吴晓波:我很认可正和岛一直倡导的“理性的判断,建设性的表达”。我觉得现在的关键是缺乏一个建设性的方式。我们在这方面,肯定会遭到很大的惩罚,所有人都会付出代价,不仅是' 老百姓(' 603883,' 股吧)。
我把财经领域分成三类,分别是宏观、微观和中观。我现在所在的中观领域是最繁荣的,包括产业经济、' 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创业浪潮、技术变革。
微观和宏观部分其实都缺失了。微观部分是企业管理。这部分的缺失是因为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精细化管理所获得的效益远远不如创新、投资所获得的效益。这不光是中国的问题,全球最近这十几年来,除了传统方面的平衡积分卡,管理学上几乎没有任何的突破。
宏观现在没有讨论的空间。
问:上一轮改革开放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思想解放为先导,改革开放又促进了进一步的思想解放。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是什么关系?
吴晓波:早期的改革开放建立在对既有秩序做破坏的基础上。我在《激荡三十年》里曾写过,“所有的破坏都是正义的,所有的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它是这样一个过程,要敢于破坏既有的秩序,甚至要敢于违法。
小平同志在1978年、1984年、1992年带来了几次思想解放运动,推动了人们摆脱旧秩序——向新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做转移。但是到后来,思想解放在商业领域所产生的效应会逐渐地降低。在解放环境下如何做建构,这是能力问题。
其实我认为现在不存在一个思想解放的问题,而可能是在10年或者20年里,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建设之间到底该怎么重构?这些是更具体而微的专业性问题。
 企业家被鼓励是挺糟糕的一件事
企业家被鼓励是挺糟糕的一件事
问:去年以来,出了很多关于企业家的利好政策,企业家都很振奋。您觉得这一系列政策能实质性改变企业家的地位吗?
吴晓波:我觉得不能,因为企业家不需要这些东西,企业家只需要一个公平的、没有差异性的市场。他们不需要被偏护,他们创造财富的热情不需要被激励,其实在这件事情上被鼓励是挺糟糕的一件事情。
问:前几年我们做过一次调查,问题是民营企业什么时候能与国企取得平等待遇,当时大家的答案不太乐观。您的观点呢?
吴晓波:如果从国有资本角度思考这件事情,其实取得平等很快。比如说我有一个“蓝狮子”(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大股东就是国有企业,我只有30%的股份。大家没有觉得“蓝狮子”是国有企业,没有人说我是国有企业的经理人,也并没有觉得它对我们有多大的伤害。国有资本不会刻意要把企业搞坏,它仅仅是一个股东而已,在董事会里面没有绝对的优势,在资本层面上都是一样的,大家按投票来解决问题。
企业层面的心态不同,国有企业是亲生儿子,民营是野生的。因为国有企业有的时候有一个威权所带来的溢价能力,比如说在' 视频牌照这个问题上,它是有1%的否决票的。在这个意义上,它根本就不可能平等,你不给人家这1%,你就没法进入这个行业,但是进入以后,这个行业可能是一个特殊行业,国家是需要通过某种特殊方式来进行管制的,它不愿以投51%的方式来管制,51%会影响你的创新,它只拿1%,但是这1%也有决定权,它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机构。全世界很少的。
全世界只有一些家族企业有这样一种方式,' 美国、' 意大利的一些大的家族企业,它股权稀释很严重了,可能就有百分之二点几的股票 ,但是它具有决定的否决权,这些是制度安排,但是中国现在存在这么一个模式。
问:' 国企改革比较理想的一个模式是什么?
吴晓波:有三个概念,一个叫国有经济,一个叫国有企业,一个叫国有资本。我觉得这三者是有差别的,不应该搅在一起。未来国有企业应该叫国有资本,国企应该资本化、证券化。
未来五年,最应该从国有资本角度实现突破,通过提升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的效率,再定义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和角色。国有资本突破,我认为它应该是用主权基金的方式,参与到产业创新过程中。混合所有制改革不应该只在企业层面上,而是应该在资本层面上进行。
今天的形态就很麻烦,国有企业拿出资产来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你一个坏资产的话,不是祸害你的兄弟嘛,你一个好资产的话,就是国有资产流失嘛,这个问题没法来解决。资本层面上是可以解决的。可以按照国有资本和国家主流基金来入股,而不是我另外再去弄一个阿里巴巴。我在书里面不是写了' target='_blank' >邓亚萍这件事吗?很典型的,我觉得国家在这一层面上,在部分达成共识了。未来我们看到的不是国有企业越来越强大,而是国有资本越来越强大,成立各种各样千亿级别的基金。文化领域不也有吗?什么创业之星啊。它不会再去投资国有企业,它会投一些创新型企业,在资本层面上进行一种混合制融资。
 其实,我是一个记者
其实,我是一个记者
问:你那个时候在新华社当记者,境遇也挺不错,为什么能那么早从体制脱离出来?
吴晓波:我从80年代开始采访。有一次我给人家递名片,人家跟我讲,你不要说你是新华社记者吴晓波,只要告诉你是吴晓波就行了。那是我第一次遇到有人只是看了我的专栏知道我的,他当时也不知道我是哪个单位。
那次对我刺激挺大的,我想大概不一定需要这个title也能够见到我想见的人,所以2004年我离开新华社,但写书是从1996年开始的。此后我就每年写一本书,离开新华社已经出了七八本书。我一直很感谢新华社,我从来没有说过新华社任何的不好,第一,它分了我两套房子;第二,在10多年时间里,它其实对我没有什么约束。它一直以来很鼓励我去好好地写稿子,当个好记者。
我到新华社的时候,采访是无底线的,你可以见所有的人,你可以花很多的钱,你三个月不写一篇稿子也没关系,最后拿出一篇稿子给我就可以了,或者给我一个结论也可以。新华社当年养记者是这么养的,绝对富养的,你在浙江当记者和你在北京当记者是没有任何区别的。我记得有一次一个内蒙古的记者来看我,说我们要到西北去看一看,弄个题目吧,后来我们弄了一个题目叫《长城中部地区畜牧业发展的调查》,而且在甘肃那一带跑了三个月。
但它还是占用我时间。第一,我每个礼拜一下午还得去开周会,最简单地说,半天的时间已经不见了;第二,我是跑工业条线的,整个新华社就我一个人跑工业条线,如果不跑的话,那这条线就断掉了,所以我必须还要去完成一些日常的工作,参加很多新闻发布会、政府现场会,它会占用你很多精力,而这些对我来讲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我就不愿意耗那个时间了。
问:你一直帮企业家讲话,现在也正在迈入企业家这个阶层,但好像不大愿意接受自己的商人定位。这是一个语言学问题,因为“商人”这个词不大好听,还是社会学、心理学方面的问题?
吴晓波:对我来讲,这实际上是一个心理的自我认知问题,本质上我觉得自己一直是一个财经记者。当年写《被夸大的使命》时,我认为企业家、知识分子不可兼容。但现在我认为,这里存在一定的兼容性。
这实际上是一个心理问题,你希望你是一个怎样的人?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对吧?我希望我还是一个财经作家,就是这样的。或者说再往后面看,比如说50年后,如果你在百度搜索一个人,这个人的第一身份是什么?我想我肯定不会因为说我办了一个企业被人搜索。
我自我认知还是一个记者,其实我一直是个在非虚构领域里的财经记者。我以后被记住,也是因为我记录了某些事情,在我记录的过程中,我一定会有我的立场,在书里面有无数我的立场存在,大概就是这样的。
至于我的企业家身份,要感谢这个时代给我机会创办一个民营出版社;我有了自媒体后,又有机会更深入地介入到商业。我并不排斥金钱,也不排斥企业家这个身份。如果在心理上有一个排序,我会首先认为,我就是一个财经作家。
问:回到初心上,您好像一直比较向往纯学术性的生活。
吴晓波:其实也不是。我觉得我对商业的复杂还是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和警惕,比如说当年做“蓝狮子”的时候,并没有那么大的纠结。出版是一个特别慢的行业,比如我们要出版一本书,快的八个月,慢的两年。我们住在一个小楼里边,一共就二十来个人,可以一起吃吃饭。那时也没说要融资,每年赚的钱,股东分掉了,我们从第一天起就没有亏过钱,就开始挣钱。所以我觉得“蓝狮子”当年是一种很安静、很古典、很文人状态的创业。如果我不做自媒体,在蓝狮子状态下,其实现在也挺好的。但是搞了自媒体以后,节奏很快,占用了我大量时间,其实它让我特别的焦虑。
还会面临利益上的问题,比如有人在吴晓波频道插了广告,他给了我100万块、200万块钱,当他突然发生一些负面新闻的时候,我怎么办?我现在可能能做到的是我不做报道,我不评论,对吧?但要特别勇敢地去质疑它,除非是特别重大的事情。重大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也会干,当年“达能事件”,我写文章发声,老宗(' target='_blank' >宗庆后)到现在还对我不高兴,也没有关系。“三聚氰氨”的时候,我们对蒙牛的质疑,那也没有关系。特别重大的公共利益事件发生的时候,我想这点勇气与底线,我还是有的。一般性事件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纠结,会有放弃和妥协。
 百年企业是妄想,做好当下就行了
百年企业是妄想,做好当下就行了
问:你学生时代印象最深的企业家是“廖厂长”(注:见吴晓波文章《只有廖厂长例外》)。这么多年,还有没有类似的让你印象极为深刻的企业家?
吴晓波:我接触的企业家太多了,我都挺喜欢他们,但保持一定的距离。每个人在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成功。我研究企业史,不会看一些很短期的事情。从内心来讲,我最欣赏长跑型的企业家,他们在很长时间里证明了自己的商业才能。
我可能更好奇的是人本身的一些事情,就像我最近写饿了么的张旭豪,关心的是一个33岁的小伙子突然有10亿美金之后准备做什么,他不当创业者以后,角色的转变能成功还是不能成功?
问:有一些你当年的好朋友,像罗胖(罗振宇),现在你们基本在一个赛道里。他发展的也很快,会不会给你带来一些竞争焦虑?
吴晓波:准确地说,我跟他不在一条线。大家都在做知识付费、新媒体,但跑得不一样。我做自媒体到现在为止,没有跑出财经领域,但老罗做得更广泛化。
我们对专业能力的理解不一样。哪怕在同样一个领域也不会怎么样,因为中国市场够大。
问:你节目里讲过,那时候还跟一些现在的大佬、首富在一起玩儿。你会羡慕他们现在的声名与财富吗?
吴晓波:没有。因为我从来没缺过钱,还比他们轻松,我干嘛要羡慕他?
我很早就认为我要有钱,很早就实现了财务自由,当时讲过一句话“我再穷也要站在富人堆里”。因为做财经报道,如果我是一个特别贫穷的人,心态一定会很差。1998年我花了100万买了个岛,站在1998年那一个点上,我似乎比BAT的三个人都有钱。
但我现在回看他们从小到大的过程,会觉得商业是一个挺伟大的事情。
其实商业特别煎熬人,“面壁十年图破壁”。一个和尚天天在山里面思考人生,通过折磨自我肉体,达到一种极限状态,对人生有一种新的感悟,商业不需要这样(就能达到这种状态)。
有200个人堵在你门口,你怎么办?有人说要拿20亿美金收你51%的股份你怎么办?你进入到一个陌生的行业,杀进去,不知道能赢还是输,你怎么办?企业家是天天处在一种极限状态的,所以你看,一些企业家到七八十岁以后,讲出来的话和老和尚没区别。
我是不反商业的。商业的不确定性不是人造出来的。军事家、政治家、哲学家、诗人、画家、企业家,被逼到一种极限状态,对生命、对世界的理解基本上差不多。像当年这些企业家,今天还在不断地迭代。
所谓商业之美是在两层意义上:第一层意义是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产品,改变社会和世界,让人产生愉悦感和成就感;第二是在改造过程中,把自我的生命逼到了一个极限,形成了一种突破。
问:现在很多企业说要成为100年的企业,成为伟大的企业。您觉得怎样才能成为伟大企业?
吴晓波:百年企业是极不靠谱的。没有一个行业是百年不变的,除非不扩张,写下祖训,不允许开第二家。只要大家还在吃火锅,你家火锅还好吃,就还能延续下去,你要扩张就变成了' target='_blank' >海底捞,就变成了另外一个逻辑了,所以百年企业这件事是极不靠谱的。你如果永远做一个庙宇装修的公司,你可以做成金刚组,你要做很大那就不行了,要把金刚组做成世界500强,你试试看,会成为一个千年企业吗?你很快就死掉了。成长特别脆弱,所以这个是不存在的。
作坊能够百年,企业是不可能百年的。中国企业家不要想做百年企业,好好做个当下的企业就满足了。
“当下”这两个字能够延长到10年、20年,我认为' target='_blank' >任正非的企业观是非常正确的,人是会死的,企业也会死的,随时准备迎接死亡。我们人活在今天不也是因为这样?
如果老天跟你说你能活600年,我现在忙个屁呀。我们说努力工作,人生就那么几年就要退休了,所以必须好好干,抓紧干。
问:你写了这么多的企业史,面向未来,有哪些期待?
吴晓波:我只讲商业领域的期待。
第一是互联网变成基础设施以后,所有的商业文明都会重建。现在的新零售、知识付费、社群经济、制造业的柔性化改造,都是建立在互联网基础上。
第二个期待,所谓的第四次浪潮,是基因革命、' 新能源革命、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带来一种推动。这些技术又会成为下一轮产业的基础设施。
这刚刚开始,未来20年的变化可能比互联网过去20年带来的变化更大。过去20年是物理状态的改变,我们原来在线下买东西,现在到网上买东西;原来用纸币,现在用支付宝。未来我们会被AI干掉,连劳动机会都没有了。我开玩笑说我们现在因为劳动而获得收入,20年之后我们很可能需要支付成本,才能获得一个劳动机会。
问:最后一个问题,您在财经写作方面的雄心和目标是什么?
吴晓波:一本书的终极读者是时间。现在我去很多城市宣讲《激荡十年,水大鱼大》这本书,其实我并不很care这本书到底能卖多少,当然能卖到100万是一个让我自己开心的目标。因为我已经有两本书《大败局》、《激荡三十年》卖过100万册,如果这本能再卖100万,那么在财经写作领域,全中国大概就我一个人写的三本书都卖过100万册。有人要赶过我,可能需要10年时间。《大败局》是18年前的书,去年还印了10万册;《激荡30年》是十年前的书,去年也印了10万册。如果这本书(《激荡十年,水大鱼大》)10年以后还能印10万册,那我认为这本书就成功了。如果这本书今年卖了100万册,明年印了两万册,后年没人印了。那其实也没有什么好高兴的。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正和岛。文章内容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和讯网立场。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请自担。
想了解更多关于《吴晓波:我们现在工作挣钱,20年后要花钱买工作 》的报道,那就扫码下载和讯财经APP阅读吧。

 客服热线:
客服热线: